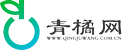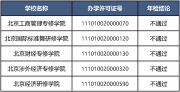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在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之下 在藤校做穷学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波士顿邮报在2015年曾报道过美国精英高校里的寒门贵子,在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
原标题:在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之下 在藤校做“穷”学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波士顿邮报在2015年曾报道过美国精英高校里的“寒门贵子”,在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之下,这些寒门并没能完全融入,他们在校园里苦苦寻求归属感,最终结果可想而和。精英学校的偏好自成立以来就注定了。
踏入哈佛校园的第一天,Ana Barros便感到格格不入,来自“寒门”这几个字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惊叹于繁茂的榆树林,古典的鹅卵石街之余,她有些抬不起头。她想:一个来自纽瓦克的女孩并不属于哈佛大学。
Ana Barros和家人们住的房子很不起眼,而且还是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资助的。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勉强维持着生计,很少能有余裕购置生活用品。Ana Barros的父母在她出生之前,从哥伦比亚移民到纽约。在家,全家人说的是西班牙语,Barros在上学以后才接触英语。Barros个子很矮小,颧骨高高的,有一头茂密的秀发。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了,她收到了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入学邮件。她说:“那一刻我明白,我从未像父母那样吃过苦。”

Barros在大一这一年选住单人宿舍,倘若要和来自特权阶层的学生住在一块儿,她会觉得很别扭。“你随处能看到自己与他人的阶级差异,从你的穿着到你说话的方式,”Barros说。她现在已经是一名社会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了,坐在学院宿舍餐厅外的公共空间,天花板高高地悬着。大一大二的时候,Barros在课上很少发言,因为怕发错音,她能通过阅读理解那些复杂的词汇,但很少有机会大声说出口。如果她真的说错了,也并不会有人来纠正她。班级里很快就有了各式小团体。“友谊是基于你的消费能力,当你没什么消费能力时,你很难有朋友。如果有人喊你一起吃晚饭看电影,你得赶紧答应下来。”Barros说。她很快和另外两个家境差一些的学生走近了,似乎她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更多些。同学们谈论着买200美元的衬衫,或是计划去异国度春假,这都让Barros感到无法融入,她认为那些学生想不到自己会给其他人造成怎样不悦的感受。最近的一堂社会学课上,Barros的导师要求学生们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定位,并进行讨论。有人称自己来自中产阶级,有人称自己属于上流社会。尽管Barros已经习惯上课发言,这一次她还是选择沉默,关于社会阶层的讨论让她感到不适。她说:“向同龄人承认自己的贫困实在很痛苦,谁想站起来在课堂上孤零零地说这些呢?”
于好几代人而言,踏入藤校是全国最精英家庭孩子的特权。但2004年,为了实现学生群体多样化,让 的“寒门”学子们有机会接受藤校教育,哈佛大学发布了一项改变丛林规则的经济援助行动:如果“寒门”学子有藤校资格,学校买单(1998年普林斯顿是第一个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援助的藤校,2005年耶鲁大学也随哈佛大学做出了一样的决定)。年收入低于40,000美元的家庭可申请这项援助,但最近门槛已经提高到65,000美金,申请通过后,学校可为贫困家庭提供高达15万美元的补助金。藤校们纷纷开放经济援助项目后,这种“零家庭付费”补助形式,让无数“寒门”学子走上了顶尖大学的“镀金”之路。Pell补助金给家庭收入高达贫困线250%的学生5,700美元,给身处四口之家的学子约60,000美元。获Pell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也被认为是反映低收入人口数量的重要指标。在哈佛大学,各种花销差不多是58,600美元,Pell奖学金只是经济补助的很小一部分。去年,19.3%有入学资格的哈佛学子获得Pell奖学金,比例比11年前提高了80%。在布朗大学,15%的学生可获得Pell奖学金,耶鲁的比例是14%。
全额奖学金进入藤校的确扭转了“寒门”学子的人生,然而这只是第一关。一旦进入校园,这些学生会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异化感,甚至自信心直线下降。尽管受到种种优待,免了学费和住宿费,保住了工作等等,这些“寒门”学子还是无法拥有足够多的零用钱,仍无法与自由支配钱包的同龄人平起平坐。其中一些学生认为,他们无权向同侪,或者学校行政人员投诉任何事,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作“忘恩负义”。
“这是很颠覆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二年级生Ted White表示。White出生于波士顿市郊的Jamaica Plain地区的工人家庭,并以荣誉致辞生的 身份,从海德公园的新使团高中顺利毕业(他是该校高年级中极少数的白人孩子)。White的父亲是MBTA公交车司机。White说,从一开始他就感到哈佛大学并不适合像他这样出身的孩子。同学们在大一就自己创业,或者为非盈利组织工作(他说,这通常得益于同学父母的资源),这让这位拔尖的学生怀疑自己在哈佛是否有归属感。他感到所有人的起跑线大不同。比如,White很感激学校能为贫困家庭的新生免费提供新生舞会的门票,但他们需要在另一列队伍领门票。“这太明显了,暴露出谁领的是免费门票,而哪些人不是。”White说。很多人意识到类似的窘境,哈佛大学的发言人表示,学校正在努力补救类似情形。和其他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们一样,他把入学考试看做是家庭脱贫的第一个重要关卡,有时候,White还是会怀疑自己来哈佛是否是正确的选择。
Stephen Lassonde,负责学生生活的哈佛大学系主任表示,第一代“寒门”学子特别要强,他们一直在和自己的身份较劲,并试图高于自己的社会经济背景去生活。“尽管我们试图让他们感到融入,但他们的室友们和同学们仍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排除在外,有些并不是故意的。”他说。
如今,White已是一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是哈佛大学初代学生会(First Generation)的副主席。他呼吁,为那些父母从未上过大学的学生们创造积极的制度变革。Barros则是主席。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这个学生会成了哈佛贫困生的避风港,“first generation”并不意味着贫穷。在2014年首创该学生会的Dan Lobo表示,当贫困生们意识到自己是家庭中第一代踏足“精英校园”的人,而不是意识到自己有多困苦后,他们也就愿意承认融入过程的辛苦。Lobo出生在来自佛得角的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在Logan地区附近的宾馆工作,父亲是厨师,母亲是服务员。为了切换到“哈佛模式”,Lobo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某天,在和两个境况相近的同学共进晚餐后,Lobo意识到这群人是校园里“隐形的少数群体”,不管是交友还是学业,他们都进行得都格外困难。Lobo决意要自己站出来,以初代贫困生的身份组建初代学生会。他倡导人们公开讨论社会背景对大学经历的影响,试图去创建一个鼓励校园变革的社区。Lobo表示,那时候人们对初代贫困生的处境只字不提。他在获得 荣誉学位后,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帮助有色人种的孩子进入精英高中私立学校。“哈佛虽然接纳了我们这群贫困生,但等我们真的到了那儿,他们也不知拿我们怎么办。”Lobo这么说。
耶鲁和布朗大学的贫困生们则建议,学校管理人员能够做更多事来培养他们的归属感。2014年,耶鲁大学开始实施本科初代贫困生学生会(Undergraduate First Generation Low Income Partnership)。在布朗大学,三个学生,包括来自加州的墨西哥裔美国学生Manuel Contreras,在2014年1月创办1vyG,为初代贫困生提供社交人脉网络(network)。Contreras的队伍在今年2月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会议,汇集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和管理人员,彼此分享信息,并相互学习经验。“布朗并不是为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存在的。”认知科学专业的Contraras经常这么告诫其他成员。“但我们必须把布朗也变成我们的布朗。”
这些团体在校园里寻求曝光度,期待更加公开的讨论,尽职的校方工作人员也为他们提供支持。这些团体还策划了一系列活动,确保藤校能倾其最丰富的资源让弱势学生享受资源支持。初代生们认为,如果藤校的基础设施默认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趋同,那么校方就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例如,有些学校在春假期间不再营业,这一行径就是没有考虑到有些学生无法负担度春假而留在校园的情况。尽管学费、住宿费等已经被减免,一些大学的收费名目,从几百元美元到一千美元不等,这个数字仍让贫困生战战兢兢。
Rakesh Khurana是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在皇后区长大,父亲是Bronx的一名教师。他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学生在校园里更自在一些。”为此,他近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去年12月,哈佛大学任命了两位初代生作为联络员,一位在财务援助办公室,一位在职业服务办公室,为了帮助部分学生的身份过渡。今年1月,来自缅因州的初代生,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生Jason Munster被称作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初代生导师”。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且很困惑,Munster正是那个能帮助你的人。Munster的本科就是在哈佛念的,他同时也是哈佛初代校友网络(First Generation Alumni Network)的联络人,该协会和初代学生会同时期成立。
尽管如此,学生们仍指责哈佛大学在初代生方面的决策太过迟疑,比如为初代生在大一入学前提供“过渡期”项目,一直没做起来。Khurana认为,这样的指责不成立,学校仍在考虑怎样才能为初代生提供最周到的帮助。“我们的专案组一直在思考,如何为这些孩子们创造最好的环境?什么是最理想化的?我们能不能更早地让孩子们建立联系?某些财政援助是否能简化?我们的目标是尽早填补这个鸿沟。”
一月中旬的某个礼拜天,在Providence西区Waldo街的一间破旧的三层公寓里,18岁的Alejandro Claudio刚刚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袋。公寓的门廊有一座圣玛利亚雕像,隔壁是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冬歇以后,学校和住处只有15分钟车程的距离,但对总穿着棕色汗衫和红袜队帽子的Claudio来说,布朗大学离他成长的街区隔着一条银河。在校园里,他就像身处山顶的完美世界,家里的焦虑被抛在九霄云外。Claudio的妈妈在日托上班,爸爸是一位焊接工,两人拼命工作,勉强付房租和水电费。主修社会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Claudio很明白,他必须成功。“如果我失败了,我不得不被打回到贫困线,去工厂打工。我得拿到好成绩,找到好工作,争取足够丰厚的薪水来养家。”
Claudio的宿舍明亮又有窗户,从那儿俯瞰,就是一片带绿荫的方院,他还可以随时在Ratty(校园餐厅)用餐,学校奖学金包含了他的餐费。他在大一第一学期时,跟朋友们坦诚地说,自己从没吃过沙拉三明治、烤羊肉串或咖喱,朋友们讶异的表现仿佛看到Claudio有五个脑袋。Claudio八岁那年从多米尼克共和国移民到美国。“我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我们每晚都吃相同的食物:米饭、豆类和鸡肉。”他说。
在Providence的拉美裔中央高中,Claudio以荣誉致辞生的身份顺利毕业。在那时,他暗下决定,他不想在父母工作的海鲜工厂做工。当他遇到辩论队教练Dakotah Rice时,他确信他能逃离西区,这位教练同时也是布朗大学的初代生。他俩常约在中央车站正对面的汉堡王,讨论Claudio的未来去向和他去布朗大学深造的可能性。“他了解我的背景,我们连着聊好几小时,我该如何踏入布朗大学,他总表现出一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可以的样子。”Claudio说。现如今,Claudio终于踏进布朗大学的校门,却看到了自己和其他学生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他误认为拉丁裔或者非裔的学生会与他的背景相仿,聊过几次天以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和白人同学一样富有。在起初一次吃冰淇淋的社交活动里,有位学生提到自己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接着问Claudio的家境,当Claudio告诉大家父亲是一位焊接工时,对话尴尬地戛然而止。在那个学期后半段,他向一位家境优渥的同学吐露,他妈妈正向他要钱支付账单,那位同学表示抱歉,这让Claudio的心情更糟了。从那以后,他不再在公开场合袒露家里的近况。
这群初代生们放佛迫降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在这里,许多孩子能轻而易举得到非常精英的实习机会,通过他们父母的名望,并能理直气壮和教授据理力争,“寒门”学子们感到了自己的劣势。即使他们身处全国最精英的学府,而他们的社会背景仍主导着他们在校园里的发展。研究表明,中上阶层的孩子们更善于在校园里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可用的资源。而“寒门”学子们更习惯于自己处理事情,因为他们很少能得到父母那辈的帮助,无论是指点家庭作业,或是大学申请等事务,同样地,他们也很少去写作中心,或教授办公室寻求额外帮助。Yolanda Rome是布朗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院长助理。她表示,许多贫困生在论文得到C后,哭着去找她。当问及学生是否和教授聊过时,回答经常是否定的。“我们正努力在改变校园文化。”她说:“这些学生们得明白这一点,寻求帮助并不成为他们的弱点。”
Anthony Jack和Jason Munster一样,是哈佛大学的常驻导师,正在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是精英校园里的贫困生。他说贫困生每隔一周会出现在他办公室,发泄校园生活的挫败感,或者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我怎么才能被引荐进一个团体?”在他的研究中,Jack着眼于“特权穷人”,也就是就读精英私立高中的贫困生,“双重弱势”群体,以及对精英高校规范不熟悉的学生群体。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学生在精英校园的成功,和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有紧密联系。比如,他们踏入校园时,是否和其他富有的同学们一样有自信,以及,他们是否意识到,与教授建立良好的一对一关系对未来工作或学业上的引荐有益。
Jack表示,“特权穷学生”比“双重弱势学生”更能适应校园文化,后者认为教授是很遥远的权威存在,在接近教授时他们表现得小心翼翼;然而“特权穷学生”更像中上阶层的学生那样,能和教授建立联系。Jack会告诉自己指导的学生,你值得花费一位教授的时间。
不情愿寻求帮助是否会影响毕业率?在藤校也许影响不大,但在全国范围内,初代生的学士学位毕业率只有11%,而藤校贫困生的毕业率激增。从I’m First收集的数据来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线上初代生社区中,98%的人群可以在6年内从四年制的学业中毕业,在布朗是91%,现实比例可能更高。
布朗毕业生Renata Martin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踏足校园时,才知道纽瓦克地区是多么贫困,她的父亲是披萨外卖送货员。她说,她希望有治疗师解决自己的身份挣扎问题,并且想用校园健康保险来支付,但她付不起15美元的共付医疗费。Martin靠着90,000美元的Jack Kent Cooke奖学金进入布朗大学,他说:“布朗大学预设每位学生都负担得起额外的小费用,比如共付医疗费,但事实上我们付不起。”在最拮据的日子,她会去找校园里的牧师,申请资金买负担不起的课本,或者货架的公车票。“寻求帮助真的很难。”她说。“但我不得不告诉教授我的故事,否则我毕不了业。”
Beth Breger是Diversing America领导企业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每年为100名 “寒门”学子提供帮助,让他们进入大学。它们的学生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度过了七个星期,来学习领导力相关课程,参加有关写作、标准化考试、准备和校园生活等方面的研讨会。他们能够接触校园内的多种资源,比如职业规划中心,他们在那可以学习如何联络和准备面试。“我们的学生有能力胜任学术作业,但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校园社交和文化上融入:比如为什么很有必要和学术顾问和教授见面约谈,怎样进入医疗中心的系统。我们不想让他们觉得利用好资源是不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有着类似的面向新生的“过渡”项目。Breger说:“这关乎孩子们的自信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公司律师,或是华尔街交易员。他们的家人没办法给他们展示这样专业视角的场面,我们想拓宽他们的视野。”
当Junior Juilia Dixon踏入耶鲁大学Trumbull学院的咖啡厅,负责快餐窗口的厨师把汉堡翻了个面,说:“嗨,Julia小姐,我今天能为你做什么呢?”Dixon戴着黑框眼镜,涂着日本茄子颜色的口红,她生于乔治亚洲的农村地区,家里11个孩子,她排行老二,一家人靠着粮票过活,这些离耶鲁大学似乎十分遥远。她每每看到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都感到很亲切。有一次,她父母租了辆车,开来参观她的校园。父母们面对Dixon的朋友们显得很不安,但却主动向餐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问:“你能帮忙照看下我的小女儿?”父母愿意寻求帮助的是餐厅工作人员,而非学校行政人员或者教师,在本质上和从大一起困扰Dixon的身份问题一模一样。
Dixon常常将自己割裂成两个身份:一个是“乔治亚Julia”和“耶鲁Julia”,这点连她父母都感觉到了。念大学的三年里,当Julia第二次回家探望父母时,父母在吃晚饭时提出自己的担忧,害怕Julia受到的教育会让她从父母身边割裂开来。“我不想你因为我们感到羞耻。”父亲说。起初,Dixon不会和父母聊起她在学校的经历,比如课业难不难,或者手头紧不紧张。打那顿饭以后,Dixon意识到,其实只要大方地和父母聊聊自己真实的困扰,她和父母才不会生疏,尽管那些困扰在父母听来都很陌生。
贫困生们在藤校校园也许会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渐渐觉得自己在家也无法得到归属感。布朗大学的一位发言人Rome表示,“通常,来了藤校的这些学生们会想家,回到属于自己的群体中去,然而藤校生活带给他们很多改变,从遣词到外形,他们也不再属于原本的家了。”
Ellie Dupler是耶鲁大学一名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棕色的卷发,戴着银色圆环耳钉,这是在学校资助的土耳其之旅的途中买的,她和自己的单身母亲一同住在一辆拖车里,直到她念小学六年级。念高中期间,她去了一所比家乡任何学校都要好的公立学校,那所学校离她家大概是两小时公车的距离。“我在等经济援助的支票呢,所以最近只能少吃几顿饭。”她说。尽管囊中羞涩,Dupler表示,耶鲁给了她一种财务安全感的假象。“老实说,我在耶鲁待得越久,我只会越来越不觉得自己属于低收入人群。”
除了打三份工以外,Dupler还在学校的滑雪队。她母亲在她家附近的滑雪场操纵缆车,因此Dupler得以免费滑雪。当她和滑雪队队友提起这段经历时,队友们感到很诧异。Dupler最好的朋友跟她说:“如果你不提,我永远不会知道你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这位朋友来自纽约市一个富裕郊区,并在她需要帮助时慷慨解囊,Dupler表示自己会很快还她。Dupler认为,她比其他一些低收入学生更容易融入耶鲁校园,因为她是白人的缘故。“一般情况下,除非我自己袒露自己的窘迫,否则我也会被认为属于大多数在郊区漂亮的豪宅中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学生。”她说。她很乐于从其他同学眼里看到自己的样子,也许这让她相信她可以过不同的生活。
毕业迫在眉睫了,Dupler会担心自己没有耶鲁的奖学金会很难生存。“在耶鲁,我的社会阶层好像上升了,但我毕业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会滑落到原点呢?”因此,Dupler有很强烈的事业心。“我朋友常开玩笑,我的宏图伟志一周一变。”她现在想要从法律和公共政策专业毕业,最后在国际关系领域工作。
Julia Dixon说,她试图不再将金钱看做判断自我身份最重要的元素。耶鲁向她展示了一种生活,晚餐话题不必围绕着逾期的账单打转。Dixon不停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不去想自己的财务负担。“金钱教我从某种生活中跳脱出来,也许这四年给了我机会去幻想想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