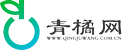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公办主导的幼儿园格局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 刚过去的2018年是教育界的政策大年,12个月间,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门至少出台了13部
原标题:公办主导的幼儿园格局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
刚过去的2018年是教育界的“政策”大年,12个月间,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门至少出台了13部与幼儿园至高中阶段教育相关的政策。2019开年的第一个教育政策直指幼儿园,称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2017年底,国内数个民办幼儿园接连被曝出丑闻后,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日趋严格。尽管在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定义中,幼儿园可被办成营利性的,但2018年的一项政策断绝了营利性幼儿园上市的道路,也使相关的已上市企业大受损失。此外,民办幼儿园的市场也在缩小,官方文件称,到2020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

▲ 2017年,携程亲子园(幼托所)被曝有老师喂孩子吃芥末、恐吓甚至殴打,后掀起舆论巨大的声讨。上海长宁警方后来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携程亲子园实际负责人郑某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同年,红黄蓝幼儿园也出现虐童案件,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通报,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女,22岁,河北省人)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遂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刘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然而,人们的观感暂不如此。在北京等大城市,公办园数量少,学位难求,让孩子就读家附近的民办园是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尽管它们往往并不便宜,有的每月收费数千元;一些家境优越者会选择设施“高大上”的高端园;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价格低廉、质量还过得去的幼教服务曾为许多劳动者缓解燃眉之急。
一些自媒体把新政解读为“私立幼儿园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扭曲了文件的意思,但一系列政策透出的气息很明显:留给民间办学者的空间不再像从前那么多了。吊诡的是,这种趋势实际与经济学理论相悖,学前教育在目前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
大包大揽会成功吗?根据规划,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将成为主导力量,以解决存在多年的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这个愿景会实现吗?
公办主导的体系,势必要求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投入,在人员方面,也可能需要增加教师编制。在经济下行期,这对既有体系意味着不小的挑战。
过去,绝大多数民办幼儿园自力更生,不获得财政支持。公众较少知道的是,公办体系内部,也存在着“苦乐不均”的局面,不少公办园也会“哭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在2011年曾发表一项研究,在他的研究对象中,三分之二的公办园都获得了拨款,但示范幼儿园获得的财政投入的均值为66.5万元,普通园仅为8.59万元。25个县的县直属机关幼儿园至少获得县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三分之一,而在园儿童数却不到本县应入学儿童总量的10%。
在教师方面,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园的教师,工资都不算高,门槛也并不高。民办园常常为教师的高流动性而头疼,本地人不愿来应聘,一些优秀的师范院校的学生则更青睐公办园。许多年轻人在获得中专、本科文凭后开始任教,但过两三年就会转行,频繁的教师更换显然对孩子的教育不利,双方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来熟悉、磨合。
▲ 2018年1月,安徽亳州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生正在供需洽谈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 图虫
影响教师们选择的往往是编制,有编制意味着稳定、体面。要成立更多的公办园、提供稳定的师资,需要加大编制供应,但在近年全国严格控制编制数量、甚至“去”编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可能性并不高。公办园也不意味着所有教师都拥有编制。浙江省某机关幼儿园的园长曾告诉笔者,该园的编制定为20个,但园内共有11个班,每班需要2个老师和1个保育员,此外还有专职的园长、副园长等。编外教师流动性很强,每年只有4-5万元的收入,明显低于在编老师。
山东菏泽的一名政协委员近日也呼吁,当地公办园人员的编制数量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长年不变,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的晋升渠道受限,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强,不利于公办幼儿园的发展,也难以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
公办园由纳税人缴纳的资金支撑,依然面临尴尬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办园在极少获得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为过半的孩子提供了教育。2017年的《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年民办幼儿园接收的幼儿占所有幼儿的56%。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曾在多个场所感慨,公共财政资金99%用在公办学校,但民办教育用1%的公共教育经费向社会提供了约20%的公共教育服务,不应忽视民办教育做出的贡献。
很明显,对于民办教育办学者而言,无人兜底和庇护,市场规律决定了他们面临优胜劣汰,始终心存竞争压力,这会驱动他们聆听家长的需求、提供更符合市场需要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学生,这些特点未必都是好的,未必都符合教育规律,但恰恰是公办体系所匮乏的部分。对民办教育的监管,不应是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而应当更精细和公平。
降低门槛、增加供给更为迫切幼教领域的问题并不是单一的,入学难、入学贵不是同一个问题。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国内2017年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79.6%,距离2020年达到85%的目标仍有距离。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头几年,新生儿数量增加,给未来几年的教育体系带去更大压力。
目前扩大公办园和普惠园比例的做法确实能起到解决入学贵的作用,行政部门可以利用补贴加发改委限价的方式控制住幼儿园收费,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调控手段,原本按照市场规律行事的主体必然会做出对应的调整。
《每日经济新闻》在2018年底报道的一个案例称,某高端幼儿园被要求转型为普惠园,学费从每月5500元“跳水”至750元,但家长却担心幼儿园为控制成本而降低质量。过去以高成本模式运营的民办园,必然为平衡收支而做出调整,服务与原先承诺发生变化,继而催生家长与园方之间的纠纷。
业界公认的是,办一所幼儿园的门槛很高,举办者势必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主体。在好不容易迈过门槛后,发现需要转变为普惠园并无利可图,同时依然要承担高昂的租金等成本时,其办学积极性必然降低,不再追求提高办园质量,甚至选择退出。在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资本费心参与办幼儿园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将所有的幼儿园交给“公家”办又不现实,“入园难”可能会再度成为一个中心议题。限价、不允许营利可能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需要被重视。
▲ 2018年11月,山东枣庄一幼儿园学生在参加“钻洞洞”亲子趣味运动项目。 © 图虫
事实上,现实中不乏怀有办学热情并且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教育工作者,但他们往往被现有的办学高壁垒边缘化。这些壁垒不仅包括较高的硬件标准、场地要求,还包括土地、消防、卫生、餐饮等一系列环节的资质。幼儿园的办学许可不容易获得,民间办园者们办理体验也并不友好。幼儿园办学的前台是大资本在几年前蜂拥进入幼教领域,并产生了一些乱象,后台则是具有教育理想的个人或小群体屡屡受挫。
“日日新学堂”的创始人兼校长曾分享过他的经历。这是一所由家长共同管理、出资的办学机构,2006年在回龙观成立,提供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其在申请学校食堂的资质时,相关部门称需要先获得办园资质。前往办理办园资质时,又被告知先要获得土地、食堂、消防等环节的资质。更关键的一点是,学堂使用的土地属于林业用地,没有符合要求的房产证。他曾经计算,在回龙观,有房产证的房屋,一天房租约为每天每平方8-10元,可说是“天价”。在他看来,“家长的监督比政府的监督要严密得多”。
▲ 2018年12月,“日日新学堂”的学生们(小学)在观察和“研究”甘蔗。 © 日日新
此外,笔者还接触过一些小微幼儿园的办学者,他们办学的原因往往是自己的家庭不满意现存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又有一些想法一致的朋友,于是把孩子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幼儿园”,雇佣老师,家长深度介入、参与管理、实践自己的理念。由于互相熟悉,大多都是朋友关系,办园者和家长的信任感比家长和常规幼儿园之间的更强。这样的家庭幼儿园在北京至少存在百余所,但距离一个法定意义上的幼儿园太遥远,根本没有纳入政府的统计,但也经常遭遇“突击检查”。
教育是复杂的,但眼下的教育管理依赖行政审批,显得有些“简单”。在幼儿教领域,能真正保障质量的并不是房子有多大、玩具有多少、行政部门的督导结果如何,而是鼓励社会参与和多样化、给予补贴与奖励、进行差异化的督导、关注家长的意见等。弱化审批、建立监测制度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