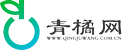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教龄14年,我两次辞去了教师编制 2023年2月21日,抱着办公室同事送的一大捧花,我发了一个煽情的朋友圈,在如此广袤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里,能
原标题:教龄14年,我两次辞去了教师编制……
2023年2月21日,抱着办公室同事送的一大捧花,我发了一个煽情的朋友圈,“在如此广袤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里,能和彼此共享这样一颗独一无二的行星和这样一段独一无二的时光,是何等的荣幸。未来,你好呀!”至此,我的十四年中学教龄彻底结束。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主动解除教师的编制。有人为了考一个教师公编呕心沥血还上不了岸,而我,转身订了去旅游的票,来到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埃及,在正午的阳光中亲手触摸金字塔的棱角,感受着凝固的时光;乘坐邮轮,在尼罗河的涟漪中,走进一座座神庙,勾画着彩色的象形文字。风吹起我的长发,它们自由飘荡着,幻化无形。这一刻,褪去一切身份标签,虽到中年,我却终于有长舒一口气的爽快。
第一次辞职,决然离疆
2009年7月5日晚七点,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轰鸣着抵达终点。刚大学毕业的我拎着皮箱,挤上902路公交车,自行回家。窗外是熟悉的城市风景,我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大四那年,我本已在北京找到满意的实习工作,并且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可十一月的某天,突然收到父亲胃癌晚期的消息,那一瞬间,困惑、痛苦、着急……各种情绪侵袭着我。一边哭泣,我却毫不犹豫打好了离职报告。在死亡面前,哪还有大事!
临近毕业,望着被化疗折磨的几无人形的父亲,我再次坚定着自己的想法,“我要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的路,我要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回家后,意外从高中班主任杨老师那里得知,母校急需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当时已错过了每年春天的考编机会,我通过学校简单的面试后就暂时代课,第二年考取了自治区直属的教师编制。
我上高中那年,是母校第一次面向全疆招生,并成立了文尖班和理尖班。我所在的七班属于文尖班,配备了全校最优秀的师资。等我再回母校,和昔日老师成为同事时,她们均已成为学校领导或者专业带头人。虽说初工作,我却有熟悉的回归感。后来,我也通过自己的认真负责,成为学校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风雅和新疆的学生
那几年,我对教育的认知也在逐渐变化 。第一年,完全没有“老师”的概念,觉得每位学生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并和他们打成一片。我曾在风雪中和学生一起挥动铁锹,清理操场的积雪,眼镜被雪水糊满顾不上擦拭;也在他们参加篮球赛被吹黑哨时,不顾自己的代课身份,带领学生浩浩荡荡一行人去找领导。学生因感动自发给我组织了大型生日会,甚至后面因为工作调整我不再担任他们的班主任时,学生还给校领导写联名信请求调回我。那一年,我最没有什么教师经验,却是我从教十几年的高光时刻。至今,我还和当时的几位学生保持着亲密良好的关系。
带第二批学生时,也许感受到学校对我的信任与重视,学校很多教职工将子女放到我的班上。彼时,只觉压力很大,我常常是学校最早来,最晚走的人。并且开始有了“老师”的样子,不自觉中和学生保持着距离。
学生在作文里写,“她的性格是开朗的。和她在一起感觉像是一个好朋友。不过当她生气的时候,那可真是太惊人了:两眼一瞪,脸一板,她的眼睛仿佛就在那时喷出火来。不过当她和办公室同事在一起时,她就立马变样了,感觉更像一个小孩子。”
记得当时,我曾因经验不足误会一个小女孩偷了同学的手机,在办公室大声斥责她。女孩脸涨得通红,却佯装镇定,微笑着说,“我没有偷!”我却不相信她,甚至因她的微笑而愈加愤怒,索性请家长到校来帮忙教育。现在每每想起,都觉得无比愧疚。
到第三批学生时,我已经在教育里找到进退自如之感。可惜那时开始负责很多行政工作,有时连正常的课堂都不能保证。但那些学生和家长,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很融洽。虽然后来因为我调动加辞职折腾了一年,没有把他们完整带到初三中考。得知我们要举家搬迁到西安去时,家长们还自发组织给我送行,席上理解和祝福的语言,久久温暖着我当时略有晃荡的心。
想辞职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是深陷于琐碎的行政工作时,我感受到一种疲惫的乏味。拿腔作调,官僚之风和僵化的思想席卷着每一位道中人。三十出头的我,尚不知天命为何物,但隐隐察觉出,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譬如笼中鸟,飞举意不忘。”某天深夜,和爱人夜谈,爱人不经意说,“不然我们去别的城市体验一下生活吧?”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我,两人一拍即合。写辞职报告,迁户口,卖房子……一切物质或声名似乎在那时变成了一种负赘,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舍离。只是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已在一呼一吸间,成为了我精神的一部分。
第二次辞职,欢然挣脱
2018年8月,我和爱人驱车沿祁连山一路向东南抵达西安。
彼时,本想在终南山下找一所普通学校安度余生,谁料误打误撞进了西安教育强区——高新区一所还不错的民办学校。生活上,也离开了自己的娘家,进入婆家的大家庭。
西安的教育节奏明显快于新疆,每天上班都是高强度,并且周末时常有各种安排。但那时,我对新生活有满满的自信和憧憬,又加上前些年的积淀,我如一条鱼把自己深深地沉入教育的最底层,和学生们同吃同学,同喜同悲。
西安市在2022年将一批优秀民办学校统一转公,这就意味着我再次成为有编制的人。同事们都很高兴,似乎退休后有了更多保障。我那时却也比较平和,好像更在意当下的境遇。
当时,国家提出要将学生分流,家长和学生都非常惶恐。大家一方面觉得这个学校还不错,孩子应该可以上线;另一方面,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状态,令人堪忧。
很多孩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残。我所在的班上,好几个孩子的胳膊上有刀子划过的痕迹,深浅不一。他们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发泄着自己内心的无助与迷茫,我看得触目惊心,但班里的学生似乎都习以为常。谈话、交心、心理疏导……多种方式尝试后,我在习得性无助里也意识到,是这个时代病了。只是孩子们抵抗力较差,表现得更明显。
2021年4月,我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一个周天,我去医院做常规检查,可结果很不好。值班女医生皱眉看着我的B超单,“这个孩子不能要!”女医生的表情很职业,但她说的每句话如重石击打着我的心。胚胎着床位置离头胎剖腹的伤口太近,已过了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孩子月份一大,子宫可能会被撕裂。我呆坐在医生办公室,久久不能回神。一个误打误撞的生命,连如烟花炫耀一瞬的机会都没有,就要被无情销蚀。我几乎是跌撞着走出医院。
回到家已八点。身子还没坐稳,一个短信进来:老师,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留恋的人。我惊然起身,一阵不好的预感如电流在大脑里窜过。是k,那个在班里很安静很规矩的孩子。我急忙给他的母亲去电。果然,孩子此刻已经爬在窗外的空调机上,家长正在哭泣劝说。努力压制内心的慌乱,我给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张主任去电简单说了情况,又叮嘱家长一定不要离开孩子,随即拉起爱人就陪我出门。
k就住在我家对面的小区。轻推开他的家门,孩子母亲正在客厅木然站着。孩子卧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了。“你怎么出来了?”我着急问她,母亲蠕动着嘴,“我出来拿手机……”从厨房可以看到孩子的身影,小小的他蜷缩在29楼的空调机上,如一只受伤的鸟,似乎一阵风就要带走他。
物业、消防先后来到,他们负责悄然打开孩子反锁的房门,我就透过厨房窗户宽慰孩子,和他聊天。三四个小时,我说了很多很多话,“怂恿”他去卧室拿根烟抽,还“邀请”他陪我去楼下喝杯酒——“因为我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看到这世上的一缕阳光,明天就要逝去了……”k从一开始的决绝到后来泪流满面。他哪里舍得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只是这世界给他的光亮太少了。父亲常年在外地做工程,回来看到他的成绩就骂“你怎么不去死”!即使哥哥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他的妹妹此刻还坐在客厅玩手机。
我慢慢从厨房移进他的卧室,又靠近窗户,窗户前放着一张书桌。“把手给我”,我试探着伸长胳膊。此刻,窗外的k好像我肚中的孩子,我把全部的爱与期待都凝结在颤抖的手上。k犹豫着,眼神略显摇摆,但好像感受到我手上的热量,他转过身来捏住我的手,我没有丝毫犹豫,拼尽全力,一把将他拽进房间,两人同时摔倒在地。
后来和k聊天我才明白,虽然我平日在k身上花的精力并不多,但他时常感受到我对学生的用心。当时,班上有几个男孩,他们的成绩徘徊在升学线下一点,努力一把就可以上高中,可他们太贪玩,对我的种种苦心并不以为然。反倒是旁观的k因此很受感动,在绝望时,他顾念着我的真心,并因此重新点燃了自己的生命之光。
这一刻我才感知到教育的魅力:如东风所到,不必让世界都和暖,但总有花朵因此绽放。
神奇的是,隔了一周,心有不甘的我再次来到那家医院,挂了妇产科主任的号。“你这个胚胎虽然位置不好,但是在细微之处,可看到它的生长方向,是朝伤口的反方向,所以应该没问题。”主任轻抚着我的肚皮,一边用仪器仔细窥探,一边说出这段如天籁的话语。
为什么一个个健康活泼的生命在接受完所谓的“教育”后,却对生命如此绝望?k 的事情并不是个例。不需要我呈现相关数据,只看国家已经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就知道有多少孩子不堪生命之重!有多少家庭在无力的内卷中人财两空!有多少老师一边看着台下昏沉的学生一边疲劳又木然地继续板书……
克里希那穆提说:你必须全神贯注于自己受限制的情况,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完全解脱,而那些束缚和限制才会自然从你身上消失。
当下的教育环境,让我感受到无奈和无助。我想,人生的基础是自由,而终极的自由正来自于意念和想法。我在心里默念,我要拿回生命的主动权,我要找到自己内在的核心力量,我要让自身能量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在领导的惊异里,我递交了学校转公后的第一份辞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