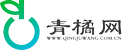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曹文轩:如何让中国文学走进世界?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这个主题可以转换为: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也可以转换为:
原标题:曹文轩:如何让中国文学走进世界?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这个主题可以转换为: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也可以转换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跨越文化。我不知道我的作品算不算已经“跨越文化”了?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即便是说已经“跨”了,大概还有一个漫长的“走进深处”的过程。不仅是我要面对这个过程,几乎所有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大概都要面对这个过程。“走出去”与“走进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状态?坦率地说,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己更加努力,将我们的作品写得更好、更超凡脱俗,一方面还需要等待——等待对方消除对中国文学的隔膜。这种隔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明里暗里已经存在很久了。消除这种源远流长的隔膜可能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我既是一个写作文学作品的人,也是一个研究文学作品的人。我看到,我们有些作品在艺术质量上已经算得上是“上乘”了,而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其境况却显得有点过于平淡,而对方一部质量平平、并未超出我们这些作品甚至还低于我们这些作品的作品,却在中国迎来了比在它本国还走俏的盛况。我们一直在以毫无保留的、欣赏的,甚至是仰慕的心态面对着国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而他们是否也像我们这样做了呢?这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当然,责任也不能完全推给对方,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将太多的时间留给了国门的闭关,中国成了他们的一个未知世界,一个他们需要暂时在洞开的大门外溜达、探头向里张望的难以确定的世界。我们需要做的,是很有风度地倚在大门的门框上,做一个优雅的动作:请进,那里头也有好看的风景。
作为还算是幸运的中国作家,我有百余本作品被翻译为40种文字,去了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罗马、莫斯科、东京、马德里、开罗、开普敦、德黑兰……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不敢保证我所分析的原因和这样的结果是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这是我要特意声明的。也许它们走到那些地方纯粹是机缘巧合,是误打误撞,或者是另有原因而我却根本就没有作出确切分析。我甚至一直在疑惑这些作品是否已经“走进去”——有深度地走进去。尽管这些作品获得了十多种大大小小的国际文学奖,尽管其中有些作品甚至一周在畅销的排行榜上。
所以诸位姑妄听之。

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会是别的,一定是文学性。
文学是有永恒的基本面的——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些基本面就一直存在着。文学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它的变法应当是在基本面之上的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法。我常喜欢拿普通事物来喻理。比如,我说椅子: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说,椅子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定义是:一种可供我们安放屁股的物体叫椅子。这就是“椅子性”。如果,这个物体不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实上,椅子也一直在变法,我们能说得清楚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椅子吗?四条腿的,三条腿的,两条腿的,一条腿的,没有腿的;还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材质又有多少种风格的椅子呢?但变的不是性质——再变,也不能变成剑——一把立着的剑是不能当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试试!
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
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学理路来进行的。因为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的背景的,它们来自于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我选择了我理解的文学的天道。我更相信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理解。后来世道变了,变得有点凶,有点古怪,“逆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深刻的标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颠覆的。如同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所说的那样,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已经死去的欧洲白色男性统统退场。因为,这些男性代表了从前的文学史,他们是西方文学的道统。文学的标准被人为地、强制性地改变了。
但我很怀疑这些新的标准。我的怀疑还因为我看到这些标榜依据“新标准”写作的作品,早已纷纷露出了败落的迹象。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其实是永久存在的,就说上面提到的椅子。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椅子那样的东西就不存在了。也许会吧?也许那时,人们就不会有让疲倦的身体坐下来歇歇的需求了,也许那时人们就不再有坐下来喝茶叙旧的闲情逸致了。总而言之,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的身体永远是直立着的,再也不需要坐下了。这一天何时到来呢?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不在了,电脑不在了,甚至互联网都消失了,椅子还在吧?
其实,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旨罢了。
我一直认为:文学与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将它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来论。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儿,在《诗经》里,在《楚辞》里,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里,在《红楼梦》里,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里,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见解:今天的一个英国剧作家写的作品必须要比莎士比亚写得好——莎士比亚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将作品写得那么好了,你,一个今天的英国剧作家,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莎士比亚写得好吗?若没有比莎士比亚写得好,你还写它干什么?你该干其他事情去了,扫马路去,或者送快递去。可是,泱泱一部文学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它所显示的景观是: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高耸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惟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是与文学的昨天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一旦分开,下游的河床就会干涸,五谷歉收,饥荒就来了。我们没有感到饥荒的临近吗?
文学有文学的边界,就像权力有权力的边界,国家有国家的边界。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数百年、数千年的战争,差不多都与边界纷争有关。古罗马有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就是测量土地,确定边界。我们都还记得卡夫卡的《城堡》里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测量城堡的边界,村庄的边界。“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既是文学就必有文学性——恒定不变的品质。我会提醒自己: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守住边界,才有可能使你的作品从今天走向明天,走向世界。边界与无疆,大概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辩证法中一对哲学性范畴。
我要说的第二个话题是:作为小说家,你必须要写一些结结实实的、角度非同寻常甚至刁钻古怪的、美妙绝伦的故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小说才算得上是好小说?我的标准是:经得起翻译。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小说才经得起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讲了一个品质上乘的故事的小说。
从前,我们将语言看得至高无上——语言至上。我对语言非常非常在意。我对自己说,你要对每一个句子负责。但我并不赞成语言至上论——至少在小说这儿。我们显然将语言的功用夸大了。是的,我们讲究语言,可是这样的讲究,只是在我们的母语范畴。如果我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日语,你在汉语中追求的那一切——比如神韵、节奏、凝练和所谓韵味,还能丝毫无损地转移吗?大概很难。即使这位翻译水平再高,对你在语言方面的追求再心领神会,都是难以做到的。他只能做到“尽量”。如果翻译之后的作品,依然会在语言上让与他使用同样语言的读者称道,由衷地赞美那部作品的语言,那其实是在赞美那个翻译在使用他的母语时所显示出的语言能力。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为中文之后,我们其实已无从知晓他在俄语方面的独到运用和美学追求以及俄语的种种——其他语言并不一定也有的若干美妙之处。但,我们在阅读了他的那些被翻译成汉语的巨著之后,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从心灵深处认定他是一位光芒四射的文学大师,是一座耸入云霄的文学高峰。翻译成中文的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也许因为语言的转换,损失了一些,但这些损失不足以毁掉一位大师。那么,是什么保证了在语言转换后的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呢?是因为贵族的庄园还在,四大家族还在,是因为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辽阔宏大的俄罗斯故事。那些富有物质感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从俄语世界转换到汉语世界而消失。娜塔莎将要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心潮澎湃。而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给她准备一套礼服,只能请女佣们将母亲的一件衣服加以改动。就在她穿着这件还在缝制过程中的衣服时,父亲出现了,她一时忘记了女佣们还跪在地上为她缝制裙边,激动地跑过去要亲吻父亲,将还没有缝好的裙边又扯开了。这个细节,或者说这个事实,无论怎么翻译,都不会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改变的。
所以,要好好讲故事。那些深刻的题旨,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暗含在和活在故事中——所有一切你希冀达到的,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有品质的故事。
当然,我承认:也许在诗歌这里可以讲“语言至上”。诗歌其实是不能被翻译的。诗歌一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它原有的韵律、节奏等,基本上都不存在了——翻译诗歌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世界永远处在运动状态,运动就有事件,而有事件就有故事。故事先于文字而产生。创作故事是一种人类的先天性欲望,而听故事也是一种先天性的欲望—— 一种强烈的欲望。“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从当时尼安得塔尔人的头骨形状,便可判断他已听讲故事了。”我们从中国的那尊有名的“说书俑”雕像的那副神采飞扬的样子,看出的却是那些在听说书的人的入迷神情。《一千零一夜》中,机智勇敢的山鲁佐德正是利用故事的魅力,从暴君的屠刀下救下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少女。听故事的欲望,鼓舞了说故事的人,使他们总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去说故事。说故事人之间开始了无形的竞争——这样,故事离小说也就越来越近了。
我们即使一眼就看出了小说与故事的区别,我们还是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故事是小说的前身;小说无法彻底摆脱故事;小说必须依赖故事。故事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肌体中的最高要素”。尽管福斯特从内心希望小说的“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小说还得老老实实地将故事作为自己的基本面。故事是小说的本性之一——本性难改,改了也就不是小说了。
其实,故事就是存在状态的模型,就是存在的写照,而文学既然呈现了存在状态,还有什么比它更深刻更重要的呢?
而结结实实的、富有物质感的故事是经得起翻译的——好故事也一定会被他人认为是好故事的。
让我们记住这个朴素的道理:“一个男孩盘腿坐在墓碑上”,无论翻译成何种语言,这个事实都不可能被改变。
我要说的第三个话题是:文化是民族的,人性是人类的。
深谙小说奥秘的一流小说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没有如此认识或者说有了如此认识却无法深切了知人性的小说家们,被稍纵即逝的时代风尚、一时名声大作的社会问题、或一些蝇营狗苟的功利性的目的所裹挟,未能进入人性层次,则永远地被定格在了二流、三流的尴尬位置上。
当我们能够始终聚焦于人性又能透彻地理解和精准地把握人性时,我们的作品事实上已经领取了走遍世界的护照。
曹雪芹、陀斯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等,都是描写人性的高手。
人性是复杂的,但复杂的人性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人性不会消失或出现新的人性。人性不变——如果变了,不再了,人就不是人了。从前的人性和现在的人性相比有变化吗?没有。至少,1000多年前的人性与今天的人性相比没有丝毫变化,不信我们可以去看1001年问世的《源氏物语》。至少,300多年前的人性与今天的人性相比毫无变化,不信我们可以去看300多年前的《红楼梦》。因人性是相通的,你的作品又写了人性,那么,你的作品自然也就可以从昨天走到今天。作为经典,《源氏物语》和《红楼梦》至今还被我们阅读,就是因为它们写了深入我们骨髓、一如既往还在我们血液中流淌的万古不变的人性。
这个世界上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但却可能没有白色人种的人性、黄色人种的人性、黑色人种的人性。无论是哪一种人种,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至今,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未发现有一种人性只属于白色人种,或只属于黑色人种。不同民族的人性自然也是如此相同——无论是哪一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民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俄罗斯人、雨果《九三年》中的法兰西人、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德意志人、《围城》中的中国人,他们各自的文化自然是俄罗斯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中国的,但人性却是人类共有的——他们都是具有同样人性的人。所以这些作品可以畅通无阻地走遍天下。如果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能够跨文化,那么他要做的就是他的笔触要直抵人性的层面——那是通向天边的暗河,你扬帆而下则可行驶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并不否认文学对人性的净化作用,不然我为什么写作。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这样定义了文学:文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现在我只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人性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人性的基本维度——爱恨情仇等,是永远不会减少,更不会被消除的,若减少、消除,就会如上所说,人将不人。文学只是让爱恨情仇等基本人性越来越正当,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是我们所希望、所向往的。数百年、数千年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目的,不然我为什么赞美文学?赞美一部人类的文学史?
中华民族曾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块土地曾屡经蹂躏,哀鸿遍地。如今,它日行千里、意气风发,正不分昼夜地创造人间奇迹。它的强劲崛起甚至让还沉睡在从前记忆中的世界感到炫目和不适。我们曾经的遭遇都将或已在转化为文学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是独特的,而独特是文学存在于世、流播于世的理由。但清醒的中国写作者心里明白:现在话题的重心应当不是“讲中国故事”,而应当是“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既是一个中国作家,他是不可能讲纽约、伦敦、柏林、巴黎、罗马、开普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的,他只能讲中国故事——北京的故事、上海的故事、云贵高原的故事或者东北夹皮沟的故事。关键就是——对中国作家而言,对中国文学而言,怎么讲这些比比皆是、犹如钻石一般闪烁光芒的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作家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分野之处,是一个作家——一个特殊知识分子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分野之处。我们手里抓着一手好牌,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将这一手好牌打烂,这就看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运行在文学应走的金色车辙上,能否坚持文学的根本规律、基本原则、文学的基本面、文学的文学性。讲,大讲特讲——凭什么不讲?不讲就是渎职,就是愚蠢,但一定是在文学的框架里讲,并一定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讲,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世界的。唯有如此,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不是了解,是喜欢,是羡慕,是钟情,是长驱直入精神腹地。中国文学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建构,是有永不枯竭的写作资源作为保证的,而且这种资源是优质的,是中国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