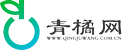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为什么今天我们更加需要鲁迅? 《鲁迅》 如果现代文学的名人堂只有一个席位,那么入选的作家毫无疑问是鲁迅。 尽管他在生前身后都不乏争议
原标题:为什么今天我们更加需要鲁迅?
《鲁迅》
如果现代文学的名人堂只有一个席位,那么入选的作家毫无疑问是鲁迅。

尽管他在生前身后都不乏争议,但若论创造力、思想性和国民度,目前还没有哪个现代作家可以和鲁迅比肩。鲁迅和鲁迅文学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在本期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钱理群,探究鲁迅和鲁迅文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
来源| 看理想节目《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
对谈人| 李浴洋、钱理群
1.
从边缘到中心的中国观察
李浴洋:您今年已经85岁了,您和鲁迅相伴已经有将近70年的时间。我想知道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您对于鲁迅的阅读、接受或阐发,大概分为几个阶段?
钱理群:我真正认真阅读鲁迅,是在中学阶段(虽然最早的接触是在小学),主要是读鲁迅小说和散文,和戏剧家曹禺、诗人艾青一起,并列为我最喜欢的三大“现代文学家”。
因此我对鲁迅的认识是从“文学家的鲁迅”入手,而且当时并没有把他放在特殊地位。这是中学阶段的鲁迅观。
1956年上大学,同年出版了《鲁迅全集》,我就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购买了这套新出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全面、系统地阅读鲁迅作品。
1960年大学毕业,我去往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当时我做了两个选择:首先是定下了“当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现实目标,同时,又立下“研究鲁迅,回到北大讲鲁迅”的理想目标。所以我对鲁迅真正的研究和对鲁迅精神的关注和把握,是在我到贵州以后。
毕业后我回到北大读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我在北大整整讲了21年的鲁迅。又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开始了独立的鲁迅研究。
李浴洋:您曾经概括过,大概以21世纪即您退休前后为界,此前的1980到1990年代,您主要是一个鲁迅的研究者。
而到了2000年以后,确切的说从90年代后期开始,您就转向以鲁迅为资源,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社会实践,用您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这一点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钱理群:这首先是基于我对鲁迅思想的实践性、当代性的认识。研究鲁迅如果脱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当下的现实世界,那么跟鲁迅是隔的。 我认为鲁迅是具有当代性的,而且有很大的实践性,或者说我是用鲁迅的方式,和当代青年发生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做这样的选择,也有一个自我反省。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批判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与传统文化、世界文明彻底决裂”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
我又没有进行后天弥补,就形成了先天的知识结构的缺陷:第一是不懂外文,第二是古代文化修养严重不足。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
这样的“研究者”,是很难真正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的——因为鲁迅是学贯古今中外,有着浓厚的文人趣味的。我缺少这两者,研究到一定程度就深入不下去了,这是我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实践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
到了新世纪,我积极投入了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运动、民间维权运动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等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鲁迅的资源。
我之所以后来在青年中影响越来越大,跟这些是有关系的——是鲁迅把我和当代青年、和当代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觉醒人生》
李浴洋: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1978年您考取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研究生时,是带着一部30万字的鲁迅研究的书稿前来考试的。那么现在回过头看,贵州和北大这两个精神基地,究竟在您的生命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钱理群:当年我离开了贵州,到了北大,但我没有忘记贵州的这些资源。而且把贵州的资源和北大的资源结合起来。
这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观察中国的方法:在中心到边缘、精英到平民之间,自由地流动,来观察中国。所以我觉得我对鲁迅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理解有许多独到之处,这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我在贵州和北大之间流动的经验。
这样一种从内部,而且是从底层到中层到上层的观察中国的方法,我觉得在当下都还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2.
今日大变革的核心是解中国之谜
李浴洋:在我看来,所谓“钱理群鲁迅”,即钱老师对于鲁迅资源的独特运用,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实践性,或者说把鲁迅转化成了行动的力量。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获取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便利性和选择性都会大很多。那么在您看来,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相比,鲁迅对于今天的独特启示和价值是什么?
钱理群:研究界有一条重要的史料发现:1930年代日本学界在翻译、介绍《大鲁迅全集》时,对鲁迅作出了两个重要评价。
第一,要解“中国之谜”,必须读《鲁迅全集》。第二,鲁迅对“中国之谜”的解读,不止从纯文学的角度,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文学角度。这两点对今天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今天的中国世界正面临“历史大变革”,这一“历史大变革”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现当代的中国,也就是如何解读“中国之谜”。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之谜”已经成为当代的民众、知识分子,也是当代的青年,最感到困惑的。
鲁迅怎么解“中国之谜”?根据我的研究,他有四个方面的反思:反思以儒家的现实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中国的皇权体制;反思中国的国民性;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 鲁迅这四大范式依然是我们今天求解“中国之谜”的很好的切入口、突破口。
还有一点,解“中国之谜”不仅是中国的民众、知识分子、青年最感困惑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中国学的核心问题。所以我反而觉得,现在更加需要鲁迅了。
李浴洋:我知道您近年来也在关注中国的国民性,进行相关研究。您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最新思考?
钱理群:我有一个思考:大陆的中国国民性和海外的中国国民性好像不完全一样。那么大陆的中国国民性有什么问题?这是我思考的中心。
这里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我写的这么多文字,实际产生影响的是一句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人知道有钱理群就是因为这句话;很多朋友对我说,“钱理群,你写这几百万到千万字的文章,最后还比不上你这一句话”。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这句话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当代国民性的核心问题。当代很多问题都是出于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选择,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觉醒人生》
李浴洋:我注意到您经常把鲁迅和周作人并举,特别是最近几年,您提倡要做周氏兄弟的综合研究。您不仅在研究中长期关注鲁迅,也写下了《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这样一些开创性的著作。
您为什么特别强调把鲁迅和周作人放到一起讨论?引入周作人,对于我们理解鲁迅有什么帮助?反之,以鲁迅为参照,我们又能照出周作人的哪些遗憾和经验呢。
钱理群:我先概括一下学术界对鲁迅、周作人的认识评价,基本有两个层面。
一是强调周氏兄弟思想根底上的一致性:都以“立人思想”为基本关注与追求,始终坚守“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在我看来,这也是“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基本命题,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力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但同时,学术界也几乎一致地指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行为方式、历史决策的选择不同,特别是面对民族意识、民族危机的时候。周作人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分道扬镳。
在此基础上,我又有新的深入,我更关注把他们看作一种有意味的参照,他们更深层面生命形态选择的差异、矛盾、困惑,超越了民族、国家、时代,显示了人天性中的悖论。
我由“鲁迅——周作人”自然联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两个典型。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是世界型的人性的两端,“鲁迅——周作人”也是超越了具体国家民族而具有人的本性的方面。
因此我认为鲁迅—周作人体现着“人类天性中两个根本对立性特征”,都是“人性的旋转之轴的两极”。也就是“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的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
李浴洋:在周氏兄弟之间,您的选择是否也有某种倾向性?
钱理群:这是很明显的:我更多地受到鲁迅的影响。这自然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个性原因。
在我看来,鲁迅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的“精神界战士”,是一种强者的选择,追求的是“非常人生”。周作人所作的是一个“凡人的选择”,追求“寻常人生”,他更适应于“和谐发展”的时代。
而我一生也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度过,我内在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决定了我选择了鲁迅式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道路,自觉追求“非常人生”。
但我内心深处,却又充满了对“个体的,审美人生”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发生人生选择上的微妙变化。特别是到了老年,我就逐渐自自然然地对“寻常人生”的“凡人选择”产生浓厚兴趣。
这些年,我经常挂在口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日常生活”、“闲暇人生”这些话题,其实都是周作人的命题,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就转向了养老学、幼儿学、未来学,倡导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
我也因此加深了对周作人思想的认识:他倡导的“生活的艺术”,是建立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之上,是一种“生活的现代化要求”,具有“未来因素”。
当然,鲁迅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可以说,到了晚年,周氏兄弟的影响就逐渐在我身上融为一体了。
3.
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李浴洋:我们讲了那么多鲁迅的意义、鲁迅的价值,但在我们充分肯定他的同时,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鲁迅的不足?
钱理群:我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我对鲁迅有一个判断: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首先,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者、批判者,他的广度和深度在现代中国是无可比拟的。第二,鲁迅更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人——他不仅是反叛者、质疑者,同时又是继承人。第三,鲁迅也留下了他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不准备简单地用“鲁迅的不足”来概括,这是由鲁迅思想特点决定的。
鲁迅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反乌托邦性”,他着力于引导世人“正视淋漓的鲜血”,着眼于“现实”的存在,而将“未来”悬置。你看鲁迅作品,从来看不到他谈未来,他是有意地把未来悬置起来了。这是和周作人很大的不同。
我们都被鲁迅的不屈不挠所感动,但我研究鲁迅越深入,越觉得我很难做到他这样。我就想鲁迅为什么能够不屈不挠地反抗,我的研究结果是, 鲁迅是仰仗着他个人的超强的意志力。
所以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是带有更根本性的,他具有一种超强的个人意志力,因此他能扛住,不屈不挠。而这样的超强意志力,一般人做不到。
鲁迅依靠超强意志力,他同时就不会寄托于彼岸的关怀和信仰。这是和我的精神气质有差别的:我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有彼岸的关怀。
而这样的彼岸关怀与信仰的缺失,又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所以鲁迅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彼岸关怀和彼岸信仰的根本性的弱点。
所以今天我不谈鲁迅的不足,而是看鲁迅的不足背后反应出的传统文化的不足。这是我的新解释。
《觉醒人生》
李浴洋:非常感谢钱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您的鲁迅观。其实您的鲁迅观的背后是您的文学观、人生观。
我们知道您是几代青年的好朋友。您今年85岁,而我们的听众可能是25岁、35岁或45岁。那么,您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提醒的,或者交代的话呢?
钱理群: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已经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巨变。当时我就跟年轻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年龄距离我的年龄有40、50甚至60年,这些年是属于你们的。在你们面对这几十年的历史巨变时,你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哪些是我们这一代没有遇到的问题?你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在和年轻一代告别的时候,我是自觉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们对属于你们的、未来的40、50、60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想象力?对这样一个变化,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