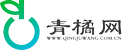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热搜上的控制型母亲,控制和爱分得清吗? 《是女儿是妈妈》 最近,曾出演电视剧《甄嬛传》的演员陶昕然,因为在一档聚焦母女关系的综艺中
原标题:热搜上的“控制型母亲”,控制和爱分得清吗?
《是女儿是妈妈》
最近,曾出演电视剧《甄嬛传》的演员陶昕然,因为在一档聚焦母女关系的综艺中落泪上了热搜。成长过程中,陶昕然不断与强势严厉的母亲对抗。生下女儿后,陶昕然决定推翻母亲的养育方式,“把爱和控制分开一点”。

许多人在陶昕然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看到了母女关系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控制。
今天的文章,作家蒋方舟将从一则经典的童话切入,讨论母亲对女儿的控制。在控诉母亲的控制之外,正视关系的复杂性和自身的矛盾性,或许是更重要的事情。
讲述| 蒋方舟
来源| 看理想节目《母亲与女儿:无限人生书单》
01.
是控制,还是“都是为了你好”?
首先从童话《莴苣姑娘》聊起,这个故事最早收录在《格林童话》里,在2010年被迪斯尼改成了动画片《魔发奇缘》。动画片对原故事的细节做了些改动,但是核心没有什么变化:
巫婆在高塔上把偷来的婴儿抚养成漂亮的少女,高塔没有梯子也没有门,每次要靠少女在窗边放下长长的头发,巫婆顺着头发爬上塔。少女从来没有离开过高塔,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男人无意中发现了高塔窗边的少女,每晚也偷偷用少女的头发登上高塔和她约会。最后他们合伙杀死了巫婆,男人和少女离开高塔,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在动画片里,虽然巫婆和长发姑娘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很明显,迪斯尼在巫婆身上投射的是一种很有控制欲的母亲形象。比如当长发姑娘想要出塔的时候,巫婆不是一味把她锁起来,而是又唱又跳地给她讲外部世界有多可怕。长发姑娘这么单纯,在塔外是不能生存的,还是母亲身边好,温暖又安全。
迪斯尼当时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对自己的女性员工做了一系列采访,让她们列出自己母亲身上黏人、控制狂、窒息的事情。所以动画片里的巫婆,不是单纯的坏人,而是一个立体又矛盾的形象,她似乎真的对长发姑娘有种母爱,她们相依为命的十几年是她人生中拥有过的最温暖、持久的关系,她也希望这个关系能永远维系。
《魔发奇缘》
这个动画让我想到去年八月左右的新闻,讲重庆一个女孩高考填志愿,母亲让她全部填重庆的师范学校,这样女孩就可以一辈子不离开重庆,在本地当老师。
女孩一开始遵从了母亲的意愿,后来发现定向师范生毕业之后必须在生源地工作六年以上,不然就算违约,要退回所有奖学金,还要赔付一大笔违约金。女孩想到六年时间,足以让母亲安排她工作结婚生子买房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就偷偷改了志愿,填了20多个外地学校。
后来女孩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但是在入学前11天,母亲偷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本,留下一张写了“对不起”的纸条之后就失联了。在失联六天之后,母亲才回家,但还是拒绝把录取通知书还给女儿,还让她归还“从小养到大的所有钱”。
好在这则新闻有个还算不错的收尾,中戏说只要女孩能提供身份证明就可以正常来学校办理入学。母亲也妥协了,同意女孩去北京,原因是在家算了卦,两卦菩萨都显示女儿可以去北京。
新闻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母亲控制着女儿的交友、饮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下的评论纷纷说“窒息”“情感暴力”之类的,许多人被唤醒了类似的经历,说自己被母亲左右着人生选择。
但同时还有另一种更残酷的说法,认为女儿不了解母亲的苦心。等到多年之后,中戏毕业、北漂无果,黯然发现茫茫世界,自己竟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所的时候,才会后悔没有走母亲选择的那条稳定的路。
《面子》
到底哪种看法才是对的呢?
我曾经问过一个刚刚为人父母的朋友,问他面对孩子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他的答案很好,他说自己无法区分孩子究竟是我者还是他者。孩子当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张白纸,所有的经验都倚赖于父母。
那么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听父母的经验,保护和过度保护、控制的界限到底又在哪里?
在我看来,区分“保护”和“控制”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看父母是否一直在塑造孩子的无力感。父母所培养的目标,究竟是让孩子越来越成熟、独立、能独当一面;还是希望孩子产生持续的依赖、对脱离父母的爱无比愧疚。
而介于“保护”和“控制”之间的“过度保护”,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急切地帮孩子过滤掉所有的负面经验,包括和人的冲突、失败的风险、他人的批评。有研究表明,越是被父母过度保护的孩子,就越脆弱,越容易被同伴欺负,这样一来,也会变得越依赖父母。
当这种不断塑造孩子无力感的控制欲到了极点,会变成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它指的是照顾者故意夸大或捏造受照顾者的生理、心理、行为或精神问题。
02.
“死妈妈才是好妈妈”?
有一部纪录片的故事过于奇特和耸动,名字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适,叫作Mommy Dead and Dearest,译成大白话就是“死妈妈才是好妈妈”。
纪录片的主角是一对母女,妈妈叫迪迪,女儿叫吉普赛。表面看起来,她们是一对非常亲密、让人怜爱,甚至让人钦佩的母女。
女儿患有白血病、肌肉萎缩、气喘等等慢性病,没有办法行走,常年坐在轮椅上,无法吞咽,靠鼻管进食,而且出生脑部就有损伤,所以在十几岁时只有七岁左右的智商。她的父亲很早和母亲离婚了,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女儿的病况,只有母亲全心全意寸步不离地照顾女儿,时不时带着她去不同的医院就医。
《死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
吉普赛很瘦小,被剃了光头,几乎没有牙齿,带着一副大眼镜。她因为病情得到了很多社会救助,她们住的房子是某个慈善基金提供的免费住房,她们去外地就医时有免费机票,还有迪斯尼的免费招待,另外还有大量来自社会的慈善捐款,邻居也给她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但是所有人——包括孩子的生父都不知道的是,吉普赛其实能走路,甚至没有生病。这位母亲不仅对女儿的健康状况撒谎,还用各种方式一直维持着女儿的亚健康状况。而一旦有医生觉得吉普赛的状况有些异常,就会换个医生。
在母亲的严格控制下,吉普赛还是会偷偷做一些叛逆的行为,比如网恋。吉普赛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孩,两人打得火热,聊天内容并不纯情。女孩会发自己的 照片,男孩让女孩叫自己“主人”。可想而知,那个男孩精神也并不正常,被诊断出有人格分裂。
吉普赛给男友买了机票,让他来自己的城市,两人计划私奔。男孩要带女孩离开囚禁的城堡,就像童话里那样,他们必须先除掉最大的障碍——“老巫婆”。
夜晚,当母亲熟睡后,女儿偷偷给男友开了门,递给他手套和刀子,男友杀死了睡梦中的母亲,女儿躲在浴室捂着耳朵。两个人拿走家中的钱,逃之夭夭。最后两人还是被捉拿归案,男孩被判处终身监禁,女孩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案件里有两个细节让我不寒而栗。一个是关于母亲迪迪,她小时候是个问题少女,父母离婚,她差点把继母毒死。后来迪迪和生母生活在一起,而她的生母无数次因为偷窃上法庭,据迪迪的亲友推测,她把自己的生母给活活饿死了。
也就是说,母亲迪迪害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又被自己的女儿吉普赛害死。这个家庭的女性好像进行某种弑母的循环,而且下一个比上一个更黑暗,也更残酷。
第二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是女儿吉普赛的表演性。社交媒体对这几个案件的总结,都是“畸形的母爱将女儿推向深渊”,可在案发的时候,那个看起来只有十岁出头的光头小女孩吉普赛其实已经23岁了。
《死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
在人生的23年中,她也一直在医生面前配合母亲的表演,并且变成了一个表演大师。虽然她和男友是性虐恋的关系,表面上她是臣服者,其实她才更像是操控男友的人。
而在入狱的几年里,她和一个监狱笔友定了婚,还经常接受采访,在镜头前妆容完整,恢复了原本的年纪,说话条理清晰,笑容也非常灿烂。
她出狱后的第一次亮相,是在红毯上参加关于自己的纪录片的首映。她还开通了社交网络账号,在Instagram上拥有超过 600 万粉丝,在TikTok上拥有超过 700 万粉丝。她的大量粉丝,也是认定自己的父母在控制自己的青少年。
我没有否定她是母亲的受害者,但我认为她在采访中的叙述实在太完整,太合乎人们的期待了,比如在监狱里,她说“比和妈妈住在一起更自由”。作为一个书写者,我太知道叙述能多么地有迷惑性,记忆又能如何进行删改,某些细节在比例上的放大缩小,就能改变整个故事的样貌。
母女相依为命的二十年,母亲已经无法讲话,所有的叙述都由吉普赛一个人完成,这种叙述多大程度地还原了全部真相?这二十年,除了受害与加害的关系,难道就没有一种母女之间的互相依赖与共生吗?
03.
“我们就两个人,我们谁也不需要,对吗?”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部描述母女间控制与纠缠的小说,那就是诺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的经典小说《钢琴教师》。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的电影,获得2001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小说的女主角叫做埃丽卡,三十岁左右,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她是一个钢琴教师,这是母亲为她选的职业,母亲从小训练埃丽卡弹钢琴,因为这是一个体面的艺术家的职业。为了让女儿专心攀登艺术的高峰,母亲在女儿身边设置了围栏,她审查着亲戚,如果哪个亲戚不中用了,就立即断绝一切往来。
精神一直不太好、老年痴呆的父亲也被送进了疗养院,不过父亲似乎没有什么离开家的痛苦,因为母亲早就禁止父亲从事很多活动,觉得他做什么都是错的。父亲或许才是强势母亲的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当母女俩把父亲送到养老院,准备离开的时候,护士让父亲挥手向家人告别,父亲没有挥手,而是用手遮住脸,哀求母亲不要打他。
埃里卡从小被母亲灌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攀登艺术的高峰。在这条路上,其他人都是竞争者,其他事都是深渊,艺术的高峰高处不胜寒,那才是埃丽卡该呆的地方,孤独是艺术大师的特权。
《钢琴教师》
不过后来,埃丽卡并没有表现出艺术大师的天赋,她只是成为了一名钢琴教师。可是母亲对她的控制并没有松懈,她每天就是工作回家两点一线,偶尔去咖啡馆坐一下,母亲便会知道她在哪家咖啡馆里,并且可以往那里打电话。所以埃丽卡几乎没有任何人际交往,她总是和别人说“我现在必须回家”。每当有人在外面遇到埃丽卡时,她几乎总是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母亲的控制下,埃丽卡甚至没有穿衣自由,因为母亲说女孩子不需要过度打扮,所以埃丽卡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但是从来不穿,只是晚上偷偷在衣柜欣赏,她拥有的只是一件件连衣裙的尸体。
母亲甚至也不想让埃丽卡结婚,她在偏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打算建一间房子,让母女俩一起过完余生,而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母女睡在一起。她说:“埃丽卡,我们就两个人,我们谁也不需要,对吗?”
如此生活了三十年,直到大厦出现裂缝。
埃丽卡有一次假期去外祖母家,一个努力打造的无菌环境被一个男人破坏了。快乐的、健康的、喜欢玩闹的表弟开启了埃丽卡对情欲的向往。她忍不住去看了脱衣舞,回到家——或者说回到母亲为她准备的育婴箱之后,因为兴奋面色潮红。母亲用嘴唇试了她的前额,发现她非常健康,“这条母亲羊水里养的鱼,养得很好”。
但已经开了的大门不能合上了,埃丽卡晚熟而压抑的性意识像潮水一样汹涌,她爱上了偷偷看色情表演,有了窥淫癖,甚至因为无法发泄自己的情欲而自残。
再后来,她喜欢上了自己的男学生。埃丽卡不断地和男学生约会。或者说,那真的叫做约会吗?我在阅读过程中非常不舒服,耶利内克用各种绵长的句子写女老师和男学生如何相互渴望、抚摸、辱骂、殴打、破坏、厌恶彼此。埃丽卡也要求男学生踢打自己,两个人的关系中没有一刻的安宁与甜美,全是暴力,精神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钢琴教师》
男学生的到来也破坏了母女之间的亲密。埃丽卡因为约会而晚归,母亲和她打了起来,两人无声缠斗,朝对方脸上抓。孩子强得多,因为年轻,而且母亲在与她丈夫的斗争中已经耗尽了力气,最后,母亲哭了。
又有一次,男学生要离开埃丽卡,说她让自己觉得恶心。埃丽卡失魂落魄回到家,和母亲躺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忍不住亲吻母亲。那不是温柔的亲情之吻,而是炙热、狂乱甚至粗暴的,就像把母亲当作男学生的化身。在电影里这一幕拍得非常有张力,是我看过关于母女关系的影像里最让我震撼的片段。
在小说的结尾,埃丽卡目睹男学生有了新的生活,视自己为陌生人,她拿出一把刀,刺向自己的肩膀。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在原稿里,耶利内克的着重点主要是在母女关系上,男学生这个角色其实是在编辑的建议下扩写的。为什么耶利内克那么着迷于写这段有些变态的母女关系呢?因为这其实是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04.
逃向母亲的笼子
和小说《钢琴教师》里的情形一样,耶利内克有个强势的母亲和精神不稳定的父亲。她的父亲是个聪明的高材生,但是因为有犹太血统,在希特勒上台后没有工作机会。二战爆发后,他才有机会加入了军工企业,但后来在工作中看到犹太人的惨状,内心倍受折磨,一直没有走出阴影,后来被送到了疗养院。
所以母亲承担了绝大部分对耶利内克的教育工作。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耶利内克被当作一个音乐家培养,她六岁开始学钢琴,进步很快,九岁开始学习竖笛和小提琴。
身为小学生,她的日程安排已经不亚于一个职业音乐家。她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练琴一个小时,然后上学,下午去音乐学校上芭蕾或者练琴。她的家在山上,是母亲要求村民把三角钢琴抬上山,那个昂贵的钢琴是是整个街区最昂贵的物品。
《钢琴教师》
母亲不允许耶利内克和他人有过多往来,就像小说里的一样,因为母亲认为女儿永远比其他人优越,所以母亲一直高高举着她超越了人群,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或者拖女儿的后腿。
母亲每天在电车站或者公寓门口等耶利内克回家,耶利内克不能参加舞会,也不能外出,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有恐慌症,只有在母亲的陪同下才敢出门。
音乐家梦破碎之后,耶利内克开始写作,她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欧洲学生运动里无比活跃,她还结了婚,丈夫是给电影做声效的,经常和导演法斯宾德合作。
但奇怪的是,两人结婚之后一直分居,她丈夫生活在德国,她则依然留在维也纳,和母亲居住在一起。她和母亲住在郊区一个小山上的房子里,社区很小,只有一个每半小时才来一辆公车的车站。母女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时间,如同双生人,一起出席戏剧首演,还分享着彼此的兴趣。
母亲不仅是耶利内克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她的保姆。客人来探访的时候,母亲又变身为女儿的肉身博物馆,复述女儿童年生活的每个细节,她记得女儿考试的题目、每门课的成绩,女儿的作品、作家同行的名字以及该人说的话。
这个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母亲去世。母亲去世之后,耶利内克再次恐慌症发作,畏惧人群,不敢去公共场合,甚至没有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
我常常在她的小说中,感觉到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愤懑与怨恨。当被问到她的写作冲动来自哪里的时候,她说:“我的创作冲动是一种巨大的仇恨,一种针对社会现实的广泛仇恨。我遭受的一切不幸,无论是男人还是私人生活,我都试图将其拔高到一个更广泛的层面。”
我想,就是这种巨大的仇恨掩盖了她的文字中其他的东西,只剩下泥沙俱下的情绪。就像是《钢琴教师》里讲埃丽卡教学生弹钢琴如抡大锤,学生们“猛击齿轮,大敲活塞,手指上下纷飞”,没有旋律、没有细节、没有爱或轻叹,只有发泄似的重锤。
可是她的仇恨究竟又来自哪里呢?比起其他很多作家经历过战争、流放、囚禁、病痛,耶利内克的命运实在算不上多坎坷,她有文学荣誉,有理解她的丈夫,有无微不至的母亲。在《钢琴教师》里,耶利内克试图把她的仇恨归因于母亲对自己的控制,可是,究竟是谁在控制着谁呢?到底又是谁离不开谁呢?
《钢琴教师》
在成名成家后的几十年里,她并不是努力想要获得自由、挣脱牢笼的样子,反而选择和母亲一起生活。她结婚之后不愿和丈夫同住,而依然和母亲在一起住,或许就是因为丈夫不能像母亲这样一切围绕着她。所以耶利内克最重要的作品是控诉母亲的精神控制,可是她却一生依赖着母亲的照顾,享受着母亲的崇拜,更享受着这种共生的关系。
或许我在耶利内克的作品里读到的那种仇恨并不是针对母亲,而是无力摆脱母亲的自己。她自己对这一点早有察觉,《钢琴教师》的开头,讲到“母亲喜欢把埃丽卡叫做她的小旋风,因为这个孩子有时候跑得飞快,她想躲过妈妈。”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刺伤自己肩膀的埃丽卡往家走,“她走着,慢慢加快她的步伐。”
埃丽卡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是耶利内克不断逃向母亲的笼子。
05.
是谁先放手
那些认为自己被父母过度保护甚至控制的朋友,可能感觉到某种类似宿命的沮丧。
父母越是控制自己的人生,就越无力,越无力就变得越依赖,越依赖,父母就越是不能放开控制的手。这种无限的循环,总得有人打破,总得有人先松手。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
从我自身来说,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我也是被母亲操纵的一生。她早早让我开始写作,我们关系也非常亲密,我对她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甚至我和耶利内克一样,都是三十多岁还和母亲一起住。
在青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和耶利内克一样怨恨,认为是母亲在控制我的人生。直到有一天,我在家看到母亲对着我满坑满谷的衣服一筹莫展,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拆拆补补,试图废物利用。我这才意识到,是我一直在控制着母亲的人生,我在用我的旧衣服、社会事务、生活琐事羁绊着母亲。
《钢琴教师》
是我在占有着她的人生。
也是我,习惯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如果仔细看前面提到的吉普赛和埃丽卡的故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当她们用两性关系来逃离母亲的时候,她们的两性关系依然是母女关系的翻版,充满了情感控制、命令、臣服于受虐。
我曾经向朋友抱怨,说在我拥有过的情感关系里,对方好像都有点大男子主义。直到有一天我看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完美伴侣》,有一句对白点醒了我。男主角问朋友为什么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控制自己,朋友说,“因为你是真空的,你在邀请别人控制你”。
我一下子醒悟,不是对方爱控制,而是因为我是真空的。当母亲作为保护者忽然消失在我的生命之后,我觉得空空荡荡,乃至恐惧,所以我希望另一个人出现能保护我、管理我。赛亚·柏林把自由分成“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按这种标准,我应该算“积极地不自由”。
再回过头来看《莴苣姑娘》的故事,你会发现与其说它像一个王子和公主合伙打败老巫婆、获得自由的故事,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悲剧:
莴苣姑娘摆脱母亲的强权的方式,是依靠另一个强权——她遇到的第一个强有力的男性,从母亲的宝宝变成了拯救她的男人的宝宝。怀了孕的莴苣姑娘很快又将进入另一个家庭,被母职的身份进行另一种囚禁。莴苣姑娘似乎一生都没有获得过一刻的自由,她可能也没有渴望过自由,她渴望的,只是更换一个保护者。
《魔发奇缘》
如何摆脱父母的控制也许不是个无解的命题,需要的是正视自身的矛盾。就像我忽然意识到:
我不能一边抱怨父母不把自己当大人,一边内心深处还认为自己是个宝宝;一边索要自由,一边要求毫无风险的未来;一边要求成年人的权力,一边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一边控诉我妈没有边界感,一边希望她的生活围绕着我转。
当我们看到这些矛盾,开始思考取舍,或许就是独立与自由的第一步。
初次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的,恐怕都很难科学精准地界定保护与控制之间的界限,该放手时就放手,不早也不晚。可我脑海中总有一幅画面是很美好很难忘的,那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小时候学自行车,总有父母把着车后座,你总以为有父母护航,放心大胆登起脚踏板,速度越来越快,享受着强风吹拂脸庞,自己控制速度与方向的快感。等你回头,发现父母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悄悄放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