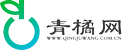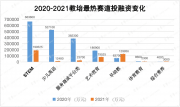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脏活一堆到手五六千,人人羡慕的大学青年教师笑不出来 5月,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自杀离世引起关注。在此之前,他未通过学校首个聘期
原标题:脏活一堆到手五六千,人人羡慕的大学青年教师笑不出来
5月,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自杀离世引起关注。在此之前,他未通过学校首个聘期的考核,亲属称其患有抑郁症。这一事件也将大学青年教师的困境又一次带出水面。
曾经,这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大学老师有编制,一年有寒暑两个长假、体面又有地位,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苦与累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即便今天,这种印象仍然存在。
其实形势早已变化。合同制、“非升即走”的“预聘-长聘制”,正打破大学青年教师的“铁饭碗”;熬夜打磨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和论文的春节,其实并不好过;一位入职北京某211大学一年半的博士后讲师此前告诉南风窗,到账的税后月薪只有7千多;舆论场上,大学教师的整体形象和地位也在滑落。

如何改善处境的话题,贯穿在高校青年教师的社群讨论里。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权威期刊学术论文篇数、申请基金项目的级别;评上“副教授”职称,是待实现的目标,也正成为“学术圈”新的准入门槛。
过程中,高校教师评价“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的痛点问题,由此显现。
挣扎求存、竞争上升中,我们发现,指标管理与量化评价之下,教育评价的标尺趋于单一,指挥棒如此强而有力,功利的应许充满诱惑,这不仅侵蚀着高校青年教师的自主性,也让他们对坚持教学、学术、科研的本心,有了动摇和分歧,进而成为大学教育向新与活力的一重阴影。
01
水课存续背后
大学校园里,“水课”让人又爱又恨
学生嫌弃它,因为内容低阶且陈旧,上过和没上过一个样,却又为了轻松拿高分提高绩点,在评奖、保研、留学中占得先机,对它青睐有加。
教学质量是教师考评的基础内容,去“水课”而捧“金课”本是应有之义,但现实中,考评却难以淘汰它。
《二十不惑》剧照
操太圣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在研究教育政策和教师教育问题时,就曾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他告诉南风窗,现行针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中,学生是评价主体之一,但学生评教却几乎失效。
“如果满分5分,大部分老师往往都是4.5分以上,没有区分度,最后流于形式。”操太圣告诉南风窗,与此同时,以“分数”为核心,教师和学生在结果上形成了微妙的等价交换关系,“学生给老师打的分高,老师给学生打的分也高,这个水课就可以常年开下去”,反倒是不轻易给高分的老师,哪怕课讲得好,一些学生也宁愿去旁听而不是选修。
在此之上,即便一些学院设置了督学督导,由行政部门、学院中层、教师之间旁听以作多元评价,但人员和精力不足,也碍于熟人社会之中的情面,效果不佳。
“其实教学这件事很难评价。”操太圣说,一位老师的课上得好不好,对学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短期不见效,也说不清关联,一个学生成才也很难说是某一位老师的功劳。
最后学校往往采用最基本的要求,“看你一学期给学生上了多少节课,有没有达到课时量要求,有没有师德师风问题,有没有教学事故,大家也就大差不差了”。相比之下,老师在学术科研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区分度更明显。
《夏至未至》剧照
另一边,以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为核心的学术科研成果是考核的硬性指标,也是教师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它不止针对教师,更首先适用于高校。
事实上,不同水平的学校也都处在追赶状态当中,“985”“211”类学校要追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院校也在申请成为硕士点、博士点,而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作为显著、易测量的成果,成为高校竞相追逐的赛道,长期以来,推就了“轻教学重科研”的倾向,也反映出了资源在往哪里倾斜。
02
考核之下,轻教学重科研
对学术和科研的倚重,通过高校的管理考核,向教师传导压力。
“学校给各个学院下达科研的指标,明确每年要完成的科研任务,学院再把指标分解到老师身上,学术工作就被纳入到行政管理当中,再定期进行考核评价,看是否达到目标,就有相应的奖惩措施跟进。”操太圣说。
这和企业绩效管理并无不同,但“胡萝卜+大棒”的方式,通过多个侧面影响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和自主性。
2019年,余薇入职一所“985”高校,“预聘-长聘”的6年考核期里,她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经历了“非升即走”。
余薇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经历了“非升即走” / 《黑狗》剧照
她在社交平台记叙了经过和落选时的错愕,“学校把我们这种已经工作3年的青椒和新来应聘的人放在一起竞争,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关注科研产出,而我还傻乎乎地分为‘科研、教学、社会活动’三方面进行陈述……事后回想,五味杂陈。”
张墨是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她看来,这所学校以教学为主,但也提出了“ESI工程科学学科全球排名前1%”的目标,且设有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张墨告诉南风窗,学校对她的考核要求,是5年内要拿到一个厅级基金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4篇学术论文。合同写明,如果没有完成,她会被调离岗位。
这套以学术科研为重点的考核不仅关系到青年教师能否留聘、入编,也和他们的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评奖评优捆绑在一起。
目标导向是明确的,也是单一的。势态也逐渐扭曲变形。
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统称为“教师”的群体并不全然授课。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前几年很多“985”高校招了大量年轻博士,进的是专职科研岗,他们的任务不是教学,不需要上课,主业就是做课题、做基金项目、写论文。如此设置的原因之一,是适应学校发展需要,体谅老师若同时兼顾教学和科研,分身乏术,两头不讨好。
很多高校招了大量博士,任务不是教学
相比之下,学校招聘的教学岗,名额有限。“但后来我们了解的是,教学岗竞争丝毫不比科研岗弱,只看教学又不行了,最后又变成了想方设法去弄一些跟科研相关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加分项。”
部分因为科研考核压力,张墨从浙江一所排名更靠前的大学转到了如今的学校,而她发现,两所学校都有“一些老师课时量不达标”的现象。
“那边有些老师不上课,是本来到手的工资就五六千的水平,也不在乎扣那点绩效的钱,自己在外面开公司做工程;现在这边的学校,一些老师会多抽时间在家里照顾小朋友,因为之前课时量达不达标,钱都照发。”但她说今年有了变化,学校增加教师课时量了,也规定不达标扣绩效工资。
03
挣工分,成为工蜂
2012年,持续关注青年群体、提出“蚁族”概念的学者廉思出了一本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在“非升即走”尚未普及之前,他就关注到了大学青年教师的困境。
“我一直认为《工蜂》深度比《蚁族》好,但是当年没什么反响。”廉思告诉南风窗,“倒是最近这几年,这本书被反复提及。”
廉思以“工蜂”类比如今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是蜂群之中的绝大多数,它们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也筑起整个蜂巢,勤苦一生。
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与之类似。“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廉思在序言中写道,而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世俗评价标准中,这些因素让这一群体在不上不下中更显尴尬。
在《工蜂》对高校青年教师、学者名家的访谈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指向“量化指标考评”。
操太圣对此也有体会,他告诉南风窗,高校会将学术期刊分等级,一类、二类、三类,要求老师在相应等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评价的时候根据论文发表篇数和等级赋予不同的分值,科研也按是申请到了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基金项目,赋予不同的分值,一本专著折算成2——3篇C刊论文,一些奖励、咨询报告最终也换算成分数进行评价,“一切东西最后都强调可见可比较”。
这种手段看起来客观公正且简单,但一如前文所述,能产生量化指标的科研学术更容易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不能产生量化指标但有价值的事情,便少有人做了。
就连“可见可比”也只是相对的。“假如本来我们有2篇C刊、一个省级项目就可以评(副教授职称)了,但如果十几个老师都完成,门槛是不够的,最后有限的名额当然给成果越多的老师。”张墨说,教师也被推着用更短的时间出更多的成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老师都要去发,博士生也要去发,这么多的作者,但是又相对小的发表空间,压力特别大。”操太圣说。
研究者的应对之法中,发不了国内等级高的期刊,就往国外期刊上投,哪怕研究的其实是国内话题;又或者为了够到考核标准,尽可能在等级低、容易发的期刊上多发几篇,以量凑分。
强大的需求,也逐渐把论文发表变成一门围绕版面费、考验人脉的生意,也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土壤。
相比论文,青年教师更愁的是基金项目申报。期刊审稿退稿周期短,还有其他期刊可另投,多少可控;国家级的科研基金项目每年就那么多,今年没拿到,只能等来年。在主管部门下发申报通知之前,许多学校提前数月就开始筹备,而春节打磨“本子”(即基金项目申请书),也成了青年教师的集体“年俗”。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青年教师连报三五年都没拿下。
相比论文,青年教师更愁的是基金项目申报 /《黑狗》剧照
数据直观显示出竞争的残酷。2023年,申请了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超过30万个,获得资助的是4.87万个,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数为4790项,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31——35岁的青年申请者最多,占比超三分之一,竞争尤为激烈。
《工蜂》当中,廉思回收了5138份的调查问卷,其中关注到一个现象:青年教师眼中,除去论文、基金项目本身的质量外,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人际关系、职称、发表费用(单指论文)、学校名气、研究方向,没有人认为影响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的因素仅仅是质量。
2012年,在《工蜂》的访谈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直言,从争学校排名到争各种“青年计划”,“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赚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工分争夺赛里,总会有人站上前排,只有少数的蜂后和雄蜂能够胜出,却以巨大的成本牵动着整个族群里的工蜂。
04
功利的诱惑与得失
从“985”高校文学院“非升即走”后,余薇去了留学过的日本找到了新的大学教职。
面试过程中,她翻译的一位日本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集,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对方饶有兴趣地问她,能翻译这位作家的书是有什么门路,她备受鼓舞。
余薇从中发现了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哪怕你是做翻译研究的,哪怕你是文学院的,文艺作品的翻译都不被认可。曾经有人劝我别翻译小说,浪费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对,可我没听,因为我是女作家粉丝。”她记叙道。
对比之下,在紧张的考核时间内,沿着“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的指标考核走,也的确助长了短期功利行为。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逼出来的一条捷径是追逐热点。去看政策热点是什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写了什么,把着期刊发表门关的编辑更容易看中哪些话题。
无形当中,老师和研究者也在让渡研究选题的自主权,然而“被选中”的同时,额外的代价却被忽略了。政策热点常常变化,切换当中,损伤的是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系统性。
基金项目也有“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这说的是,花大力气拿到了国家级基金项目或子课题,但没有在期限内完成,最后结不了项,相应的科研经费被收回,研究者被除名。但在此之前,一种怪异的行为已经出现:拿到了国家课题几乎变成一种荣誉,大家可以用它申请其他奖项、人才帽子、更大的项目,这个课题就不管了。
“如果真正是要重视科研,评价就不要只是看你有没有拿到什么级别的项目,而主要是看你怎么研究,最后做没做出来真正有学术水平的成果。指挥棒如果指不准的话,大家就会关注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作为目标本身去追求,而偏离了本质,带来很多危害。”操太圣说。
基金项目也有“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
以“唯论文”为起点,“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注:各种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才称号,如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其实相辅相成、彼此强化,沿着单一的路径,资源愈发向少数人集中,也强化了单一的成功观,由此和多元的学科特点发生冲撞。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注重论文、重视引用率、量化实证最早更多是理科的判断标准,但很快影响到其他学科。早有工科教师提出批评,工科侧重工程和应用,天天发论文那怎么行呢?时至今日,“工科理科化”的批评声仍在。
操太圣所在的人文社科同样难受,“人文社会学科看重专著,以前老先生更是如此,需要足够的篇幅不断论证辨析,一写就是十几年,思想性才能形成。现在我们以论文评价为主,篇幅已经限制了论证,也没有长时间的沉浸式思考,还说专著折算成两篇c刊。”
05
开窍和开心
《工蜂》当中,记录了一位青年教师的憋闷。
他常常要和自己不感兴趣的课题打交道,这让他倍感如芒在背。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他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他有五花八门的比喻,“简直就像上刑场”“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心里非常抗拒,即使是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
有人劝他,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回,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当学者就像开汽车,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难就难在让他转向。
《青春派》剧照
访谈者记录下他的许多语录,其中一句是:“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
开心,那不只是名和利的问题。
“我们高校教师本质上是这样一个群体,自主、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断超越。只谈要求,不顾他人的选择,蔑视人家的自主性就是麻烦的事。”操太圣说。